「都是生病害我的!」淑美在電話邊哭邊說。
淑美今年51歲,96年開的刀。因為生病治療而辭掉工作,但家中少了她這份收入後,先生卻開始惡言相向。總算治療結束,淑美想回頭找份工,沒想到卻處處碰壁。有的一聽到是生過乳癌,就明白表示不願雇用;想要找勞力方面的,卻又因為淋巴水腫,無法提重物,而讓雇主搖頭拒絕。先生看淑美整天待在家裡,經常罵她,還曾說她沒有用,該脆去死死算了!有時甚至暴力對待,讓淑美感到害怕,卻又無處可去。長久下來,淑美也認為自己一無是處,更怨恨自己曾經生過這場病,才會害她如此淒慘,有時甚至也不想活了。
有時志工接到電話不是詢問治療的,而是屬於情緒方面的問題。姊妹會打電話,通常是沒有發洩的管道,需要有人聽聽她訴苦。以淑美為例,因為家中經濟與夫妻相處,讓淑美感到自信心低落、無助、孤單、痛苦等,這些都會造成生理與心理上的強大的壓力。壓力,其實是一個隱形殺手。許多科學研究也證明壓力是造成乳癌發生與復發的一個重要因素。
志工的處理方式,是先讓淑美宣洩情緒,由談話中成為出口。接著詢問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散心的,到戶外走走,或者看電影的,暫時脫離家中的環境,遠離壓力的來源。若是在交談中發現姊妹有陷入憂鬱症的可能,或許可以建議或鼓勵尋求專業的諮詢或治療。目前各衛生中心都有提供心理諮商服務,在醫院中也有身心醫學科和睡眠中心,幫助姊妹解開心中的糾結,找到強化內在的力量,以面對家庭與婚姻上的難關。若是察覺有家暴的情形,也可鼓勵姊妹撥打家暴專線113,以保護姊妹的生命安全。
志工不是萬能,沒有辦法讓姊妹的問題消失無蹤。志工能做的,就是支持與傾聽,讓姊妹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,自己的聲音是被聽到的,自己的感受是受到接納的,自己的存在是得到關愛的。我們不能給予答案,可是我們可以提供資源,讓姊妹知道只要需要,隨時可以加以運用。當然只要姊妹願意,即便只是想要說說話,就拿起話筒,我們也都會在電話的另一端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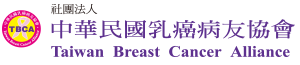
 愛波塗鴨格
愛波塗鴨格